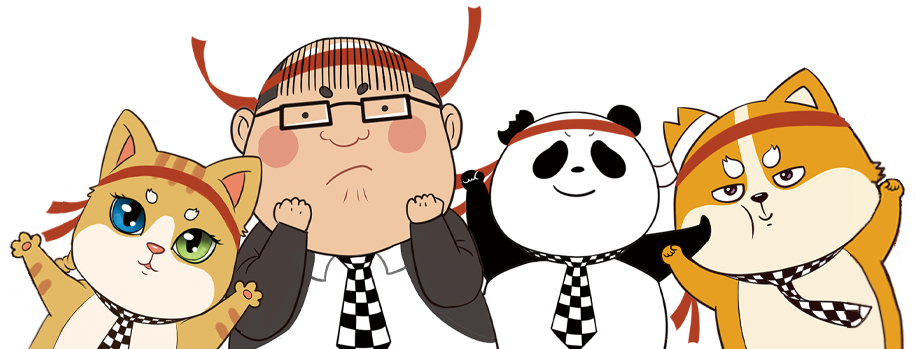正如诗人们所言。
他们尚未看清众神,如果
在挺立的草叶中
听到世界上任何一种风声,
在阳光下他们就不会惊恐
不会因寒冷而发抖,那时众神还年轻
而风却老了。
——爱德华·托马斯《深山小教堂》 杨泽芳译
我又闻到那股令人作呕的烧焦味。越过空地,我看到那个老人一瘸一拐地拎着燃烧的垃圾桶扔到腐烂的水池里。老人的动作迟缓,神情紧张,整个场景在我看来却显得优雅,我甚至在想,自己年老后要不要也找一点东西来烧。
我认识那个老人,但他肯定已忘了我。是他教会我了树机的编码语言,除了他的两位学生我与克白以外,他是这个村落里唯一通晓这门语言的人,而且只有我和克白才能明白,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。后来村里的很多老人家都说他精神不正常,按他们的说法,他着了某种业障。
在我看来比起失忆,他更像是活在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时间段,那时他还没来到我们的村落,还没认识我与克白。像个突然造访村落的陌生人,一睁眼就发现自己落入了丛林的陷阱里。或许他从未熟悉这里的环境,对他来说村落十多年如一日地冰冷陌生。但远远看着他衰老的面庞上茫然窘促的神色,我神经一颤,冒出了一些更为可怕的猜想,我甚至不确定他现在是否还能够在入梦时连入树机。
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去确认这件事,但刚走两步就停下了,意识到自己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即使他的身体真的太糟,甚至无力支撑自己的独居,我又有什么办法说服他呢?他让我畏惧,越是看着他,这种畏惧越是与日俱增。他很老了,白发像稀疏的蛛网缠在头顶,褪色的皮肤上凸起一块块的黑斑,像村子里那些曾祖父辈的老人。他本该没有这么老。但我真的明白年老意味着什么吗?明白年老的人在想些什么吗?如果我明白,我大概不会一次又一次被当作不速之客赶出来。
或许我该找克白商量一下。
我在村落的另一头找到了克白,他正在自家田中,给地里的一个铁桶生着火。看到我来,他笑着朝我招手,“刚挖出来的红薯,吃吗?”
我摇摇头,只是等着他忙活手里刚清洗好的红薯,用一根粗细适宜的树枝从一端串到另一端,像穿针一样细腻地环顾了一番后,拿到铁桶中刚燃起的火上烤。
“你最近还有去见老师吗?”我问他。
克白愣了一下神,手里串着红薯的树枝一松手掉进了火桶里,克白连忙把它捞起来,冲我打着哈哈,“你说老师,是谁?我们都多久没上学了。”
“我说教我们树机编写的老师,住在村子那边的小屋里。你很久没去见过他了吧?”
虽然我只是想问问克白,但突然反应过来自己语气中不自觉带上了一丝责怪,克白有些尴尬地挠挠头,“反正老师也认不出我们了嘛。之前和你去见他总是被当作陌生人赶出来,我以前不知道被他训了多少遍,自己一个人更不敢去,他压根不喜欢我。”
克白比我小两岁,我一直把他当弟弟看待,听到他这样抱怨,下意识想劝诫他。至少在我看来,老师对我们两人的态度并无多大差别,没有多好也没有多差。他大概也从没想过费心来厌恶我们其中的谁,就像他曾经养在院子里的那些花一样,只是他用来保持孤独的借口而已。当然,那些被他忘掉的花早已枯死。
但我只是继续问:“你要和我去见见他吗?”
半蹲着身子的克白抬起头来,紧盯着我。“为什么?”
“他最近状态很不好。”
“他后来一直疯疯癫癫的。”
“就算他不情愿,也只有我们能照顾他,村子里没有其他人会管他的,十多年来他甚至没跟他们说过几句话,他们可能都忘了那里还住着人。”
似乎是为了和我看齐,克白站起身子来,他已经要比我高出一个头了,浑黑的眼睛沾满了泥土的色彩,在午后散着热气,像一双不会做梦的人的眼睛。
“所以老师怎么了?”
“他的精神状态很虚弱,我担心他可能连不上树机了。”
“那又怎么了?普普通通地睡上一觉有什么不好吗?”
“可这是老师唯一的追求了,如果不是树机,他又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?假如他对这些一无所知,只是守着自己的一块地耕一辈子,至少他现在还是健康的。除了我们再没有人知道老师对树机付出了多少心血,又达到了多高的造诣,如果我们不管不顾,这一切都会悄无声息地结束,就像它根本没存在过。”
“所以只是你想让老师继续连上去,你自己不甘心,对吗?”克白的质询让我发怵,我向后退了一步,想再仔细看清楚些,确认自己没有认错人,但我的样子在他看来可能更像是要转身逃跑。
“所以我才觉得你变得越来越像老师了。从以前就是这样,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能够知道他的想法,无论什么时候你们都做着同一个梦。早晚有一天你会像他一样疯狂,忘掉我还有村子里的其他人,最后住进他的屋子,天天点燃自己的笔记、塑料袋、垃圾桶,然后扔进池塘里。”
“我只是想让你陪我去见见老师,如果可以的话,照顾一下他的身体。”
“你知道他压根没教给我们多少东西,你怕他死了,没人再能给你更多。”
我大概明白了为什么克白突然变得这么狂躁。
“你的树机编写遇上什么问题了吗?”
“不,我很久没连了。”
闷热的午后没有风,空气像凝固住一样挤压着皮肤,如果屏住气,沉重如铅的暑气可能就这样顺着鼻腔灌满肺底。又是那种刺鼻的烧焦味,伴随着红薯浓烈的香气,但克白低下头发着呆,没有去管。我想或许雨要来了,这样压抑的天气后往往有一场雨,冲散谷间沉积的闷热,夹杂着泥土和动物死骸顺着山坡流下,如白日的阴影般汇入河里。
我回到家时天边刚响起雷声。我静静在门前等待着,暴雨像只即将展翅的乌鸦。
母亲的声响从厨房传来,碗盆碰撞的声音,她从侧门探出头望着我,“马上要吃饭了。”
“妈你自己吃吧,我想休息一会。”
“怎么了?”
“我去找克白时在他那里吃过了,现在不饿。”
母亲眯着眼睛像在审验我说的话。
我没有继续解释,急匆匆爬上楼梯,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。
或许我还是该去见他。不该就这样被克白吓退,我不认为他的话能打消我什么念头。
暗沉气流激烈拍打着树梢与芦苇,一场浓缩的风暴正在窗外酝酿。云层发出潮水一样的轰鸣。我钻进被子,捂住耳朵想阻隔这些杂音,但不安还是从内心升起——他活不了多久了。到那时一切都会结束,以我和克白,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。
一滴雨水滴到了我的额头,不,应该是汇入了我的身体。无声无息间雨雾笼罩了身边的一切。我抬头看向天空,铺天盖地的树枝遮挡了我的视线,枝干交错间,未完工的天空在雨幕后像一团灰暗的幻影。
我回到了树脚下。
四周的一切还不稳定,蒙太奇般变换着各种形象。唯有主机树静静伫立在中央,如古老的地层支撑着梦境的延伸。雨淋在身上并没有冰冷的感觉,只是意识到雨接触到了自己。我并不知道自己在树机中的形状,这种接触感来源于两者的相融。因为一切都是同一种物质。
随着梦境的分化,周围的形状开始可以辨认。一片空旷的石砖广场上,我坐在中央,一段声音从模糊的远方传来,像原野的风声。声音越来越近,越清晰,我从只言片语中渐渐领会它的意思。它也有了形状,站立在我面前。
“制作世界的过程......一次次地在梦中重演。它由最基础的介质承载内容,结合形成复杂的知识体系。语言与图像是不同的介质,但它们都可以被用于制作并理解世界。树机同样如此,而且它更具外延性,它迅速地生长,越过一个又一个边界。当人们写下一句话后,又可能从这句话中获得更深的含义。对于树机的编写者而言,这种理解的延伸被树机的生长性数百倍、数千倍地放大。”
它像我内心中的另一个声音,在回答我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。
我将它记录下来,用梦的介质。数年来我一直在树机中重复这一工作,但今天似乎有些不同。梦没有呈现一副晦涩难解的景象,而是给了我一段清晰冷静的思考。
这大致与老师曾经在课上的某些隐晦提示相同。没有什么比梦更具可塑性,只用梦这一种介质,就可以将现实无限地拼接重现。如果掌握了这种介质编成的逻辑,便可以介入甚至控制梦的形成。将这种逻辑汇编,把编写成型的各种梦境连入庞大的数据库,在编写者共同的梦境中制作一个稳定的世界景观,就是树机运行的本质。
事实上如今我了解的这种逻辑(或者说树机语言的句法)少得可怜,只有最基本的记录功能,仅供我束手无策地观察各种无法理解的梦境。而今晚我梦到的这个声音提醒我,关于这种逻辑的知识,同样可以通过编写树机的梦境来获得。
记录完毕后,我把编写的内容细致地压缩,它逐渐拥有稳定的形状。一种对树机的认识论理解,一个新生的知识出现在我眼前。当我编写好它的那一刻,也随着树机的逻辑对它有了真正的理解,像一块拼图,被拼接在了世界本来的面貌之上,一切豁然开朗。
它似乎是为了消解我的焦虑而来。我的心脏开始谨慎而激烈地跳动,再次感到最初接触树机时那种兴奋。成长起来的主机树会指引我们的道路。我们会制作天空,制作宇宙,并由此理解它们。
我向眼前的主机树走去。我一直坐在它的树荫之下,但想要走到它的面前比看起来困难得多。仿佛每走一步,脚下的道路都在蔓延。更准确地说,我像一支芝诺的箭,每走完一半的路程后,都会面对下一个无尽的一半。如果朝着这个方向一直走,我猜大概可以这样永远走下去。但我从没试过,也不太清楚。
当足够贴近主机树时,会发现它的根基上遍布着数不清的小径,这就是编写者与主机树的交接之处。我带着刚编写好的内容往前走,进入树机迷宫般的道路群中,思考着该把新内容编入主机树的哪一部分。这时一个身影从某个拐角出现,有着明显的人形轮廓,但很高大,像披着斗篷,向我这边走来。他的手中同样有着刚编写好的内容。
或许是由于主机树内的道路太过复杂,树机的编写者之间很少能相互见面。但这的确是我们共同的梦境,我偶尔会遇上一次这样的碰面,不知道对方是老师、克白,还是某个遥远地方的编写者。这毕竟是一份孤独而漫长的劳作,能确认对方存在,对编写者而言是一份莫大的慰藉。我们都希望为树机编入更多梦境,因此这样偶遇的时候,通常我们会分享彼此编写的内容。
我将自己的造物、新生的知识分享给他,但当对方张开手时,一切并未像往常那样和谐地结合在一起,他的内容吞噬掉我的内容,随即化作一缕不可察的灰烬,消失了。我呆立片刻,意识到对方编写的不是其他东西,而是火——对于树机而言绝对的禁忌。
醒来时灰烬消散的景象依然在我眼前。我控制自己尽量不去想这件事,昨晚只是不走运碰上一个怪人罢了。一晚的梦境对于漫长的编写来说无足轻重。但这是我编写树机以来最特别的一个梦,一个可能让我找到前进方向的知识,被如此轻易地毁掉了。
夜里我很晚才不情愿地躺上床,反复确认自己是否还有什么没做。需不需要做一些笔记。我应该用一个新本子把今后的思考记录下来,一些在树机中的重要信息可能会被我轻易忘掉。但我翻遍了房间也没有一个新的笔记本,只有一些没扔掉的废纸。
我踮着脚走下楼来到厨房。整个屋子一片漆黑,像吸满了寂静的海绵,母亲打扫完厅堂后扫把被顺手放在了楼梯口一侧。我从水龙头接了一杯冷水喝下,靠在水池旁,仔细地端详着房间的构造和窗外只剩隐约轮廓的草木。
一切并没有想象中熟悉,甚至于陌生。我发觉编写树机形成的思维在影响我对现实事物的判断。几面墙的接缝本该隐匿在黑暗中难以察觉,但在我的眼中它们却如此突兀,窗外的草木、围栏,远处连绵的山、树同样如此,事物的轮廓线越来越清晰,近在眼前。这是它们的形状,我明白了,墙缝的线条构成了这个空间,而它们很轻易就会被折叠、翻转、变形,这些预示着空间尽头的线条,背后潜藏着无数个可能的形状。厨房之所以稳定保持这个形状的原因,与树机中赋予梦境以形状的逻辑很可能是相同的。并不是梦境过于变幻无常,而是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来得太迟、停留在了它的形状上。假如我们能在更“早”的阶段认识现实,是否会呈现树机的那副景象?
我洗好杯子,放在水池台上。它与台面之间的衔接更加精巧,一个完整的圆,更容易翻转,但却几乎找不到折叠的角度。假如可以找到方法将它翻转...我想起某些在梦境或想象中如此合理的形状,在现实中却不可能实现。为什么?什么东西多了出来,在我们编写树机的时候。我继续回想,一团尚未成型的混沌,形状逐渐浮现,中心是一点亮光,亮光扩大成一团火,将所有形状悉数吞噬,一切回到原点。
我有些不耐烦地揉着头发。那人在生成火,老师说过绝对禁止在树机中编写的内容,这可能会毁掉树机。我必须回去再找到那个人,或者找到其他人。编写者在很远的地方或许有自己的组织,只要告诉其中一个人,他们应该会想办法。
但只要我回到床上闭上眼,周围的那些事物的轮廓便醒了过来,在我眼睑后的黑幕中不停蠕动、变化,整个村落、河流、山脉,一齐涌进这幅拥挤的画面中,线条相互碰撞、接合、缠绕,随后被火焰燃至一片灰白,不断重复。我就这样闭上眼睛听着树梢间的风声,克制自己不再去想任何东西,静静等待这些形状平息,直到一声声吵闹的鸡鸣,以及窗台上透出泛白的晨光。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。
第二天晚间我庆幸地感到了一丝倦意,但上床不久后又再次消散。三天后,我开始为自己的这种状态感到害怕,但完全无法摆脱这些线条的纠缠。随后的一周时间里,我仿佛一只闯进某个致命陷阱的猎物,无法理解自己身处怎样的境地,树机必须要入梦之后才能开始链接编写,失眠无疑是对编写者来说最绝望的打击。
我尽量不在夜里发出声响让母亲察觉,但在无法忍受之时,我还是悄悄溜出家门,沿着河边跨越村庄,避开晚上从田里爬出的蛇,一路来到老人的小屋前。我不知道来这里干什么,除了空地上方悬挂的一轮弦月,什么也没有。小屋的木门腐朽破旧,看上去完全抵挡不住任何闯入者,但自被他赶走以来,这扇门却是我最害怕的事物之一,连走上前直视它都做不到,仿佛门后随时会出现老人那双令人畏惧的眼睛。
被失眠与无数形状折磨了数天后,我开始逐渐理解他的处境。这些线条在引诱我从现实寻找通往树机之路,说不定有一天,我真的能在现实中编写梦境,而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。这也就可以解释,他的疯狂或许是为了更深入树机的内部,而将全身心都投入到树机的编写之中,把现实割让给了梦境。这毫无疑问会给他现实中的意识带来剧烈的压迫,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压迫中,树起了他与我们之间的这层业障。
但当我像这样在深夜里一晚又一晚地窥视着他的小屋时,我总觉得这就是离我梦境最近的地方。
再见到克白时,他依旧带着笑容向我招手,像我们从没争吵过。但这个笑容反而加剧了我的不安。
“克白。”过度的失眠让我发不出什么轻松的语气,我想让他记起我们那天的争吵。
“你怎么了?”
“你最近一次连进树机是在什么时候?”
克白低下眼睛,似乎在迟疑是否要回答我这个问题。“很久之前了,或许是几个月前,或许是一年以前。”
“这段时间里你都是在做着普普通通的、看不见主机树的梦?”
“是...”察觉到我的异常,克白开始退缩,“你问这个干什么?”
“你感受到两者间有什么联系吗?树机的梦,与普通的梦?”我没有回答,继续追问。
“不就是...一个有主机树,一个没有吗?”
“我是说更深层次的,就像入梦前的一条分叉路,一边往树机,一边往普通的梦,你每晚都清醒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吗?”
“你到底怎么了?”克白像是有些生气了。
“现在只有你能帮我,克白,我陷入了一整晚一整晚的失眠,我寻不回自己的梦境了。”
“这和树机有什么关系?”
“我觉得,树机混淆了我的现实与梦境,以至于我无法像以前那样顺利地找到抵达梦境的路了。”
“我不可能帮你寻回什么梦境的。”
“那至少,你可以连上树机,警告里面的人,有人在树机里生成火。必须尽快阻止。”
“火?”
“我编写的内容被烧毁了。”
“不。”克白往后退,一次又一次地摇着头。
“为什么?克白,我能拜托的,只有你了。”
“不,我骗你的!从始至终,我压根没学会那套编码语言,关于树机的一切,我都是从你和老师那里听来的,我根本没连进树机过,我只是不想让你们发现我其实什么都不懂!从一开始我就是在含糊其辞地迎合你们!你明白了吗?!”
克白丧了气,独自一人蹲在泥地里,“我什么也帮不了你。”
我隔着一段距离、沉默地望着他,不知道该怎么开口,本应感到失落的心,却近乎卑鄙地几乎松了一口气。或许是因为这解释了克白的所有反常,也或许是因为这意味着我说服了克白——只有老师,老师还有可能帮我们。
他反常地越过了小屋前的空地,穿着整齐,扶着我母亲做给他的那根拐杖,像要进行一场远行。他很快步入午后静谧的林荫,虽然不知道他此行目的为何,但在小径中央他遇到了我们。
“老师,”面对他的疑惑,我小心翼翼地挑选着词汇,“我们有问题想请教您。”
“你们在编写树机。”他盯着两位初次见面的同行,露出了戏谑的表情。
我沉默了半晌,身旁的克白也没有出声,最后我也只是轻轻地摇摇头。“老师,我们遇到一些困难,现在连不上树机了。”
“我对你们没有教育的义务。”老人冷漠地转身跨过水渠,来到林地的另一侧,顺着菜圃向更空旷的稻田那边走去。
我想追上前,但身后被克白拉住了。他低下头,做出了一直以来打退堂鼓时的表情。从前每次看到他的这副表情,我一直以为自己内心的感情是怜悯,但到这一刻我才明白,他这副表情让我厌烦。我强硬地抓住他的手,再次拦在了老人面前。
“这些线条是什么?你肯定也能看见。”
“是文字,树机的文字。”老人意外直率地回答了我的问题。
“它们不是现实中本就存在的东西,是受树机影响才出现的吗?”
“或许一开始就有...你们知道吗,在远方曾有一个部族,他们的语言中从没有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时态区分,他们过着时间之外的生活,因此当外面的人走进这个部族,开始教给他们时间的观念时,他们不相信这是现实中本就存在的东西。但问题在于,时间是否真的存在,语言带给我们的究竟是否是真实?你对树机的质疑不就在这点吗?”
“没有人会去相信梦。”克白出声喊道。
“没有人证明过时间的存在。与时间同样,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认识,几乎全是源于远古时期的想象。那不是最古老最古老的树机吗?当它生长为我们的现实时,再没有人会意识到这点。”
“那我们现在梦中的树机,究竟是什么?主机树并不止一棵吗?”我有些呆住了。
“你们从未想过树机的来源。这棵在编写者梦境中生长的树究竟是怎么来的。”
“你知道吗?”克白问道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老人闭上眼摇了摇头。
“通过对树机的编写,同样可以追寻到树机的来源吗?”我问。
“你很聪明。假如通过不断对文字的书写,能够追寻到文字的源头,那树机同样可以,而且快得多。但或许不可以,没有人会给你答案。说不定我们从最初的提问方式就错了,事物本就没有来源与结束的说法,我们只是用自己体验到的线性观念去丈量完全未知的事物,用语言来思考语言之外的谜团。文字诞生之前,文字真的不存在吗?那我们凭借文字所理解的一切都将随着文字的结束而化作虚妄,现实比树机中的梦境更虚有其表。”
老人似乎意识到了自己话里的纠结与混乱,表情逐渐紧张、迷茫。他莫名发了脾气,不知是对树机还是对现实,也许是对我们。他挥着拐杖劈断了路边的一节篱笆,用难以置信的眼神,盯着这截碎掉的篱笆。
“有人在树机中编写火,你说过那是绝对的禁忌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那会烧毁主机树的。”
“不,你压根不懂!你说我说过?你完全在说谎!”老人像要跳起来,整个身子都被拉高了,但他病弱的双腿很快开始发抖,又接着俯下身子寻找重心。
“可我确实看见火烧毁了我编写的内容。”我有些不敢看他愤怒的表情,侧过脸继续说。
“你能明白?”老人破口大骂,“火和其他编写的梦境没什么不同,全都是梦!”
“但它出于某种原因不能被树机接纳,甚至会破坏主机树的基础逻辑框架。”
“滚!现在给我滚!”他继续挥舞拐杖劈碎另一节篱笆,空气中响起凌厉的破风声,克白拉着我后退两步,靠在一旁的树上,不发一言地望着老人。
老人没再看向我们,他像回忆起了痛苦的经历,面庞扭曲。平静下来后,他只是独自默默转过身,如一位兴致缺缺的旅人,背向我们离开。
“你从来没想把树机语言教给我们,对吗?”克白最后问向老人的背影。
老人偏偏头,像听到了,但没有在意,迈着蹒跚的步伐,朝来时的方向返回。
回来的路上我和克白没有再说话。可能我打算说些什么,但一路上积累的沉默太过沉重,当我想打破时却发现自己没那种力量。他朝我轻轻摆了摆手,没有回头,在岔路口径直走向了回家的路。
夜晚我依旧无法入眠。平躺在床上的姿势比以往更让人窒息,杂乱无章的线条拼命涌进脑海。我肯定还有什么没做,肯定还有件事在等着我去做,只要完成了,一切困境都会迎刃而解。焦躁中我不断审视着自己的大脑,大脑与主机树一样,充满了无数的小径,或许在某一个拐角处,我会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我越是深入大脑的迷宫,四周景象就越是逼真得让我目眩,难道我正在树机之外编写梦境吗?一个躲在迷宫最深处的形象越来越清晰,那是一个长年以编写树机为生的人,是他,孤独地、迷茫地站在中央。他为树机几乎耗尽了自己的一生,那他应该通过树机获得了难以想象的知识,这难道不是我始终贪婪地窥视着他的理由吗?可迷宫之后的这副形象被我毫无保留地看透,却毫无半点智慧的痕迹,只剩衰老、枯竭、精疲力竭后被遗弃的皮囊。那个树机编写者到哪里去了?难道树机最终只是,毁了他吗?
我必须见他一面。
我睁开眼,仔细确认房间内事物的稳定,以驱散掉陷入迷宫的惊惧。我一如往常般闯进夜色中,走向那条烂熟于心的小道。或许是心情过于急迫,夏夜吵闹的虫鸣和时时侵扰的幻觉让这条路变得无限漫长,每次我觉得下一拐角后就是小屋前的空地,拐过去却发现还有一大段路要走,这让我想起了走近主机树时的感觉。
最终在我怀疑自己被幻觉搞得在夜晚的村子里迷了路时,终于望见了那座孤零零的小屋。脆弱得仿佛要被月光压垮,与这个河谷中的村落格格不入,像一座数世纪之前的堡垒,被遗弃在了这个偏僻之处。
我下定决心闯进去,像一个抢夺真相的劫匪。我用尽全力推拽,木门轻易地被打开了。屋里静得出奇,厚重的灰尘和纸屑飘散在空气中,桌椅和书柜安静地陈列着,与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景象没有什么差别,书柜上的书少了很多,是他从外面带来的,如今大概都被他烧掉了。
我悄悄顺着破旧的楼梯上楼,二楼只有一间狭窄的阁楼,用作他的寝室,我只在帮他拿东西时进去过为数不多的几次。打开门时我的手有些发抖,某种恐惧和成就感在刺激着我行动。我走进去。但空无一人。只有一张简单摆放着的床,和莫名眼熟的书桌。我困惑地环视四周,担心他把我当作小偷,躲在了哪个角落。但没有,床脚,门后,书桌底,都没有。房间里没有人。
一路上的紧张与疲惫变成了失望与惶惑。晚上他会去到哪里?我守候了这么多个夜晚,从没见到他在晚上离开过。我想起了今天午后他那副要出远门的样子。难道他...离开村子了吗?我坐在书桌前,沉重地喘着气,粗粝的空气在喉咙中来回刮蹭,刺得火辣辣地疼。书桌上有几张揉成一团的废纸,我展开了其中一张,上面胡乱的画着各种线条,与我所看到的那些一模一样。
这就是他对树机的记录吗?不,更让我困惑的是——这里是老师的阁楼吗?我抬头看向房间的天花板,那些棱角上的线条依旧在不停放大,朝着某个未知的方向延伸。我似乎看到了,看到了翻转的可能——只要沿着那条轴线朝内部折叠,空间悄然翻转——我的空想便结束了。
我永远无法直接进入他的世界,他的想法,他的知识,还有他对火的痴迷。这是我自己的房间。我的床,还有我扔在书桌上的废纸。越过熟悉的窗口,在河对岸的村落尽头,主机树覆盖了大半片夜空。开始只是一点刺眼的闪光,随后在一条枝干上迅速蔓延,在天边燃起了熊熊的火焰。
“妈——”我大声呼喊母亲,尝试弄清这荒诞的处境,但没有任何回应。我冲出屋外,田野一片死寂,再没有之前聒噪的虫鸣。火焰向其他枝干蔓延,覆盖整片天空,我看见主机树的树枝燃烧断裂,像崩溃的高塔向村庄坠落。河谷的低空盘旋着灰烬的风暴,河流像平原被割开的伤口在沸腾。
我拼命朝着火的地点跑去。那颗树,我所知的唯一一棵主机树,数年来我把所有的梦境都灌注在其中,如今所有的轮廓、形状全都迅速融化,甚至连我自己的形状也在奔跑中逐渐消散,当我重重扑倒在地上时,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,已经难以分辨究竟是我观看树机的“眼睛”,还是树机本身在崩溃,也许作为被制作的景观,两者是同一种事物。
来不及了,我绝望地感到整个梦境都在急剧增温中坍缩。周围再没有了农田与河流的景象,大地不断萎缩荒芜,四周昏暗得像一个没有四壁的洞穴。我尝试向前爬行,但任何行动的力量都因为这梦境的崩溃而消失了,只有主机树还在远处燃烧着。
四周的黑暗越发沉寂,不再散起一丝波纹。这时,一个影子像从水中爬上岸般,由燃烧发出的光线投射到了黑暗中。它动作很迟缓,似乎由于只是一个没有本体的影子而迷茫,不知道自己该模仿谁。当它望向远处的那副崩溃场景时,动摇般闪烁了两下,开始朝那边移动。
不知道为什么,但绝望中一丝予感驱使我喊出声来。
“你是克白,对吗?”
随着我的呼唤,影子又一次闪烁,形状更加清晰,我确信自己没有认错。但它从我身边走过,脚步沉重,没有理会我。
“求你了,别丢下我。”我几乎对克白乞求。
影子停下了。除了移动之外我无法理解它的任何动作,它或许看向了我,或许没有。我头晕目眩,精疲力尽,只觉得自己要随着梦境一同被烧成灰烬了。口中弥漫着苦涩的甜腥味,尽力呼吸着每一口烧焦的空气。这些都是虚假的,灰色的虚假的造物。空气也好、火焰也好、身体也好,眼前所见,身体所触的,还有数年来每一个夜晚的造梦,都变得意外地荒唐可笑。但同时我也不再渴望什么现实的,坚实的信仰。或许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沉入树机缥缈的幻想,或许我从一开始就诞生在树机的梦境之中。而现在一切的答案,都在眼前的克白那里。
和老师一样,我从来没有真正看清克白,在数年来不断累积的谎言背后,在一个个共同拥有而又互不相通的梦境背后,或许反而是我,被排除在了老师与克白之外。
影子静止了很久,像在沉思,或判断眼前的情势。最终它向我走来,随着我们接触相融,我不知道自己成了什么形状,仿佛被他揣进了兜里。眼中只剩一方狭窄的天空,以及主机树上铺天盖地的火焰。
我们前行得很缓慢,眼见着视野尽头的主机树繁茂的枝节被火焰摧残得越发消瘦,像极了一个人从青壮年渐渐走完自己的一生,如今已垂垂老矣,而我们依旧在跋涉着,完全失去了时间的感知,却永远也无法抵达。
后来我们更像在攀登、在上升,在一个长长的沙丘上攀爬,在河中逆流而上。最终,我们抵达了大概是原先小径入口处的地方,燃烧着的主机树,依然通天彻地,占据了我们的全部视野。
在这颗已近荒芜的主机树下,我第一次清晰地看见了那片未完工的天空,与我想象中的近在咫尺不同,主机树离它还很远很远,远到几乎不可能触及。它像个缺口,像冒险故事中那些船员抵达的世界尽头,在那里,世界的洋流奔涌地泻入虚无的深渊中。曾经我们尝试着用编写的梦境将它填满,绽放着树枝扩张到更高更远的地方,却从没有看见过它这副残酷而不可知论的面孔。
就在这时一个梦魇般的身影在树冠处露出了半截身子,一个高大的人形。它摇摇晃晃,几乎要从树顶上摔倒下来,身上缠满了致命的火舌,却依旧仰望着天空。我望着它,因太多的未知而感到沮丧。它是如何爬到主机树之上的?它为什么要毁掉这一切?这瞬间,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憎恨,拼命诅咒着它的自私。
它在编写,我猜测,一个最后的,规模最庞大的编写。
我看不见克白,他不在我的前后左右,而在我这双“眼睛”的后面,这种感觉极为奇妙,像他消失了,或者我消失了。我开口向他问道。
“克白,我们还能回去吗?”
影子没有回答。
“说不定,我只是你的一个梦而已。”
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否让他听见,或许我也听不见他的声音。声音本就是我们形状的一部分,而它早已不知被折叠成了什么样子。我们只是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,望着树冠上那个疯狂的身影,默默等待燃烧的结束。
当主机树的生机最后一点不剩地被火焰吞噬时,整个树机开始剧烈地动摇,濒临崩溃的末尾,树冠上那个早已扭曲的身影也即将消散,但在它的手中,一个有着明确形状的内容缓缓成型,它的编写结束了。最终一切被它精确地握在手中,编成了一个转瞬即逝的梦境。
那个梦魇般的身影是他,我应该从一开始就明白,他要离开我们了,同时要带走他给予我们的一切。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人。当天午夜,整个村落都被冲天的火光惊醒。老人的小屋在黑色的夜幕下变得炽热、透明,如一个庞然大物在星宇下盘旋,穿着单薄睡衣的我在远处看着这一幕。此后我再没连上树机,我不停地梦见这个燃烧的夜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