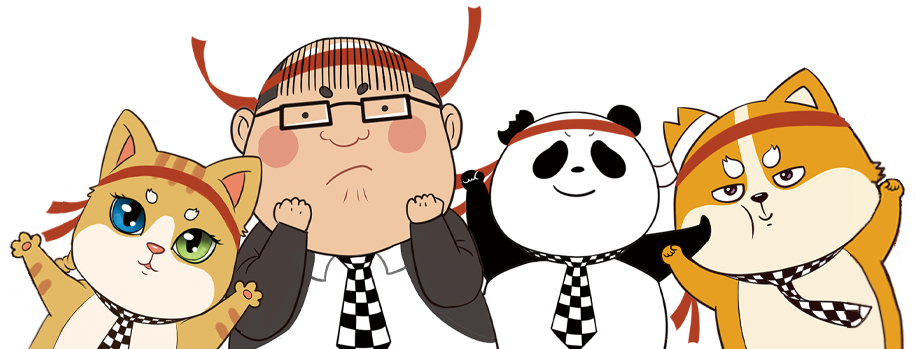深冬的冷雨萧索而尖利,垂在漆黑的夜幕里,如同一根根从天而降的笔直铁线,径直贯入泛花的积水中。
深山的雨夜全然不似城市般喧嚣,豆大的雨点劈在山野和砖瓦上,只有一片此起彼伏的低沉轰鸣声,细细听去,竟又能震得人心发慌。在这片本该是鹅毛大雪的雨中,一辆停在院中的警用桑塔纳哼起引擎,猛地睁开了双眼。
两道车灯在漆黑的雨幕里,蓦地捅出两条纯白的光柱,耀得人睁不开眼。如同是贯通太空的虫洞,或是通往某处天国的隧道。白光扫过院子,把雨线投影到水泥墙壁上,根根清晰。终于,两道光柱停在了堂屋门口。把古桥村派出所几个字映得格外清晰——这字不是印在牌子上,而是直接写在了墙上。堂屋门口大开,好似一口吞掉了直射而来的一道光柱。在门内,几个人的身影格外清晰,如同是聚光灯下的演员。两个警察——我的父亲、颜叔,还有三个村民,在强光的反差之下,只能看清他们黑色的身影。
我紧紧地抱着书,躲在门口的房檐下。没有人注意我,此刻,他们的目光都被村民刚刚送来的那具尸体引了过去。父亲和颜叔站在我这一侧,从他们穿着警服的长腿之间望去,躺地上的人没有穿衣服,身上裹着看不出材质的东西,像是兽皮。他他身材并不高,如果活着,站起来大约也就比我高一头。只是那浓密的腿毛和父亲相比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父亲半蹲下去,伸手朝向那人的脸,又在那人身上捏了捏。他应该是在翻看那人的眼睑,试探那人肌肉的僵硬程度——侦探小说里是这么说的。
“老胡,我早就说了。这他妈就不是——不是人……”
“闭嘴!”父亲吼道。他起身朝三个村民问道,“人是在哪儿找到的?”
“桥底下。”
“冬天水小,要是夏天,早给冲走了。那河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尸骨呢……”
“你他娘的给我闭嘴!”父亲冲颜叔吼道。接着,他转身朝那三个村民说,“是逃犯,案结了。过了年,十五以后到所里来,领几桶油。大家辛苦了。”
三个村民木讷地点点头,直到父亲啪地敬了个礼,他们才像是在梦中被惊醒了一样,又重新点点头,然后并排着像木偶一样,走出堂屋和院子。他们的身影穿过雨幕,消失在夜色里。
“老胡,我先给县局打个电话,让法医来一趟。”
“法医?”父亲高出颜叔一头还多,他拧着眉,一步步朝颜叔逼过去。“来一趟?”
“要不我开车,送到县局去。”
“送过去?”父亲走到颜叔跟前,低头紧紧地盯着他。“大过年的,你打算扛着个死尸进城去,或者是让人家法医来一趟?你想从这个死人身上查出什么来?嗯?你就算查明白了,能有什么用?死人会复活吗?你个大学生,不留你在县局里坐办公室,为什么?嗯?我看你是嫌被贬得太近,我看你才少根筋,你才他妈不是人。一个没名没户口的死人,你查清楚了对谁有好处?嗯?对你,对这些村民,还是对这个死人?如果真相带来的只有灾难,你还非得撞得头破血流?”
颜叔被父亲逼到了墙上。一道闪电把大地照得亮如白昼,几道漆黑与纯白的光影间,他高耸的眉骨和如刀削般的颧骨被映衬得格外明显。他正要开口,却看到了父亲身后的景象。他双眼圆睁,惊得张大了嘴。在堂屋门口,一个孩童一手抱着书,一手提着一把骨斧,被骨斧割破的手上,鲜血淋漓。他放大的瞳孔挤退了虹膜,两个黑洞一般的眼睛里空洞无神,只有眼底映出的莹莹的绿色幽光。
那是我。
这天早上。
警车驶出县城,一路朝西侧的群山奔去。我坐在副驾驶上,抱着怀里一本厚厚的科幻小说,低头翻阅着。
“不要在车上看书,对眼睛不好。”父亲把着方向盘,目视前方。
“嗯。”我头也不抬地应道,继续低头看书。
“别看了,给我讲讲吧。是什么书?”
“科幻。”
“谁写的?”
我没有搭理他,只是咕哝了一句作者的名字。
“萝卜头・锁爷?”
我轻声笑了起来,合上书。我知道父亲在想什么——他想不动声色地把我的注意力吸引过去。
“不。是个加拿大作家。讲的是尼安德特人的故事。”
一道长长的刹车差点把我拍在挡风玻璃上。我从驾驶台上爬起来,揉着红肿的脸颊,看着惊魂未定的父亲。他正两眼发直,愣愣地盯着前面。一只从路边蹿出的狗正倒在路当中。没有被车轧到,它被急促的刹车声吓瘫了。
“Neanderthal——”父亲喃喃自语道。那时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,后来我才知道,那个单词指的就是“尼安德特人”。
父亲用力眨了眨眼睛。那只狗从地上狼狈地爬起来,飞快地逃走了。后面的时间里,父亲一直没有说话。警车钻进西面的群山,萧索的北方大地从这里开始,骤然掀起狂澜,滔天的巨浪向上翻起,还未落下,便定格成了山。公路变得格外漫长,回环往复之间,仿佛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灰白色的山野让人意兴阑珊。我缩进座位里,怀中紧紧地抱着书,安全带勒在胸口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“书里讲的什么?”父亲两手抚过方向盘,拐过一道急弯。
“尼安德特人没有灭绝,灭绝的是智人。在那个世界里,没有工业化,甚至连农业都没有——他们依然在狩猎。他们都是双性恋,每十年,男人和女人才会——”
“屁话!”父亲忍不住喊了出来,他一掌拍在方向盘上,喇叭声惊飞了路边树间的几只麻雀。“你妈给你的零花钱都买了这些书?”
“妈从来不给我零花钱。你给的。”
“……”父亲伸手挠了挠他那饱满的后脑勺,似乎不知道后面应该接什么话了。“嗯……你妈也是,明知道我们年底要跑乡镇搞考核,没时间,还非要去参加什么‘学术会议’。算了,也多亏是你颜叔在这当所长,不然人家还以为我是带着孩子旅游来了。”
“你可以把我塞进后备箱。”我想起了电影里的情节。
“那直接成拐卖儿童了。”父亲打趣道。
“嘿嘿。”我笑了起来。
“寒假作业带了吧?正好这几天在这儿,把寒假作业写一写。”
“没带。”
“……等回家让你妈揍你。”
“她顾不上。”
“那我来。”
“你不舍得。”
“……”父亲被噎得无话可说。过了一会儿,他自顾自地笑了起来。“你个兔崽子。快看,那房子看见了吗?那叫自然村——自然形成的村落,少的可能只有几户人家。”
我伸长了脖子向外面望去。在两座山之间,山腰间青灰色的山石上,有几处石砌的小房子。
“要不是村村通,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进不了县城一次。”
“那他们怎么生活?”
“像人一样。”
那时,我还不明白这句话的深意。
“给你讲个故事吧。这个村子,是全县最穷的。早年间,因为山太高太险,路也没有,村民们出不来,外面的人也进不去。这些年路修通了,电也扯进去了。但要说落后,不是那么一朝一夕能改变的。你颜叔说,有一次,一个收山货的贩子,进山之后被推着手推车的村民撞了。两个人闹到派出所里,你颜叔说:
‘你看,你把人撞了吧。’
‘嗯。’
‘把人撞伤了。’
‘嗯。’
‘人家干不了活了,要求赔偿。’
‘嗯。’
‘那你得赔人家钱。’
‘我为什么要赔钱?!’
你颜叔说了不知多少遍,最后都是这句‘我为什么要赔钱’。后来你颜叔说:
‘这么着吧,咱假设。假设他在路上把你撞了。’
‘他为什么撞我?!’
‘他不小心。’
‘他没撞我。’
‘咱假设。’
‘嗯。’
‘咱假设他在路上把你撞了。’
‘他为什么撞我?!’
‘他不小心。’
‘他没撞我。’
‘咱假设。’
‘嗯。’
‘咱假设他在路上把你撞了。’
‘他为什么撞我?!’”
“呵呵,死循环。”我说道。
“对。就这么着,你颜叔折腾了半宿,也没折腾明白。”
“可为什么呢?世界上真有这样傻的人吗?”
“落后和愚昧并不可笑,也并不见得是身处其中的人所主观乐意的。”
“可那个村民,他真得不懂吗?”
“你怎么定义‘懂’?什么才是‘懂’呢?如果说,一个人,或者一群人,在他们的观念里,没有‘赔偿’的概念。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天经地义的,包括偶然事件。那么,他们会‘懂’吗?”
我抱着怀里的书,看着无精打采的落日正沉向远方起伏的群山。心想,当智人遇到尼安德特人,他们之间,也会“懂”吗?
在一处缓坡上,车坏了。父亲让我坐在驾驶室里,教我怎么控制方向和离合。他跑到车后面,闷头推起了车。从后视镜里,我看见他高大厚实的身体弓下去,像一头牛一样,顶着车缓缓前行,直到我重新打着火。当我们抵达的时候,已经是半夜了。
“哎哟老胡,你可算来了,全猪宴都给你备好了……”
“还全猪宴?只怕猪都还在圈里边圈着吧。”
“这你都知道?哎车没事吧?咱们这西山里有个邪乎地儿,车到必熄火……”
“你看我下车不打你!知道还不早放个屁?差点把我们爷俩折进去……”父亲一边倒车,一边从车窗里面骂他。
“嗨,这种邪乎事儿,你不是从来不信的嘛。再说你劲大,这车扛你都能扛来。”
“等我下车就揍你!我这不还带着孩子吗?你嫂子又忙。你说你就不能给我省点心……”
下车了,颜叔一把抱起我朝着食堂走过去。天上开始落雨点了。我四下张望,除了立在大院门口眼瞅要倒的牌子,这哪能看出来是派出所,完全就是个带着院子的民居,特别老而且破的那种。
父亲停好车,小跑着跟了进来。阴沉的夜空下面,只有熊熊燃烧的灶火透出来的光亮。
“电呢?”父亲摸了把脸,睁大了眼睛四下里看着。
“掐了。我跟供电所说,晚上就不供电了。”
“啊?”
“让他们改了线路,分了一股,给村里的学校。你放心,电费还是所里出。”
“……这羊毛薅的,真有你的。那晚上办案怎么办?”
“不是有蜡烛么。再说人家这儿民风好,晚上没案子。对了,明天跟我去学校给他们补补课,你这一趟不能白来。”
我坐在低矮的椅子上,翻开书看了起来。
“真行,摸黑看书。随你爹,亲爹。”说着,他摸索着从一堆调料瓶里摸出了一瓶。“你说,有人从上学就摸黑看书,还一看好几年,还不近视。这还有天理么……”他举着瓶子嘟囔着,凑到灶火前瞪了半天。
“那是醋。”父亲实在忍不住了。
“嗷嗷,我就说嘛,还是你眼神好,半夜看东西跟白天似的。”
“我说你是傻子嘛,你又不承认。你看不清还不会闻呐?”
“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?还是我哥聪明,脑容量也大,就你那脑袋,咱发的大盖帽,都得定制。”
“哼。你准备的全猪宴呢?这猪还是囫囵的吧,我看明天还能上街跑。”
“哎哎,要说跑——前段时间警情通报里说,是你让那个逮了好几次都没逮着的飞贼自己去投案自首了。啊?可我怎么听说是你黑灯瞎火的,半夜一个人追着小偷跑了大半个县城。人家小偷还以为是遇着鬼了,到最后实在跑不动,瘫在地上跟你求饶。结果你把手拷一扔,让他去自首,你自己回家睡觉去了?”
“我不回家睡觉我去哪?又不是我值勤,我就是起来出去上了个厕所,还给我撞见了,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找抽?我要是收不服他,以后还得闹事。他以为仗着自己一双贼眼和狗腿,就没人办得了他了?得让他有点敬畏。”
“对,敬畏。我就知道我哥牛,浑身都是长处。就比如说你这胳膊,就比我长……”
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,想起刚放假的时候,母亲带我去做棉衣,裁缝说我胳膊也比一般人长。
“你才长,你全家都长!”父亲突然没好气地吼起来。
从小到大,我从没见过父亲像今天这么健谈,我知道他们俩上大学时就是铁哥们。可这突然之间,气氛沉闷下来。我从手里的书上抬起头来。在我看来,他们的身影和我手上书上的字迹一样清晰可辨,只是此刻,两人都定在原地,手里的动作也停下了,就像被孙悟空施了定身术。我想起来,父亲曾不经意间提过,颜叔从小就没有父母,他是一位云游四方的老道带大的。
“叔!”在这一片沉寂当中,我大声叫了起来,装出那种我从来不屑的、最孩子气的声音嚷道。“叔!你知道鸟怎么分公母吗?”
”鸟?你叔连人都分不清男女,还鸟……”
“我刚看的!有个男人问法师:老婆老在家里唧唧歪歪,他应该怎么办?法师指着树上的两只鸟反问他,你知道哪个是公哪个是母吗?法师说,你看那个唧唧喳喳一直在叫的就是母的,旁边那个缩着脖子闭着眼,一声不吭聋了似的,就是公的。”
“哦,”颜叔恍然大悟般地叹道,“还是单身好啊——这一点连鸟都知道!”
“没呢,还没讲完呢。”我说道,“他继续问法师:那如果有两个相互对着叫的鸟呢?一停不停的那种。法师说一”
“哈,哈哈,哈哈哈——”颜叔笑得俯身下去,伸手抓着灶台。“法师肯定说,那两只都是公的!哈哈哈哈!”
“你个兔崽子!”父亲吼道,却没有丝毫怒意。
“老孟啊,这小子说咱俩是那两只,两只鸟啊。哈哈哈哈,老孟,这孩子比你强!”颜叔前仰后合地指着父亲,笑出了眼泪。
“这臭小子——对,比我强,那是那是必须的!”
两个人放声大笑起来,刚才尴尬的气氛一扫而光。我重新拿起书来,尼安德特人的世界重新进入视野。
“所长?颜所长?颜所?老颜!”
迟到的晚餐被一阵紧急的叫喊声打断了。父亲和颜叔放下酒杯侧起耳朵听着,我盯着眼前的糖醋豆腐(父亲做的,真好吃),心里想,颜叔承诺的那只“全猪宴”,此刻应该正在打着呼,安稳地睡在猪圈里吧。
院子里,雨一直在下。细密缠绵的冷雨,反倒映衬得厨房里格外温暖。外面的叫喊声更大了,我趴在窗前,擦去玻璃上凝结的水汽,盯着外面。一个人影摇着手电,走进院里,身后还跟着两个人,像是抬着什么东西。三个人造型怪异,穿的不是雨衣,后来我才知道,那是用麦秸、竹篾编成的雨具,类似于南方人穿的斗笠和蓑衣。
父亲和颜叔起身,一人拎了一把雨伞,拉开门,朝雨中走去。我的目光紧紧跟随着他们,来人的手电晃了晃,一道昏黄的光柱被雨打得七零八落,闪了闪,灭了 。
我凝视着雨中的几个人,渐渐地,他们的身影愈加清晰起来。我感觉,当我在黑暗中凝视什么东西的时候,瞳孔可能会慢慢变大,跟猫有些类似。我分明看见有什么东西从那担架上落了下来,没过了地上的积水里,可他们谁都没有注意。父亲弯腰下,看了看他们抬来的东西,又朝四周望了望,接着,他挥挥手,颜叔带着几个人走进了堂屋,父亲则上了车,随着引擎声,车身抖动起来。
在闪电和车灯纯白的光线下,父亲和颜叔看到了形如鬼魅的我。父亲奔到我跟前,拍了拍我的脸。我如同是被魇住了一样,梦游般地站在原地摇晃着。父亲从我手中夺过骨斧,又转头看了看那地上的死尸。他把骨斧扔到死尸身上,又脱下警服披在我身上。他在冬天从来都不穿毛衣,里面只有一件衬衣套着秋衣。他两把扯下衬衣,撕开,裂成细条扎在我的手腕上。他大步冲进雨中,回来的时候,手里拎着几瓶从厨房找到的烈酒。他把酒倒在我的伤口上,我却全然感觉不到那伤口的疼痛。他又把瓶里余下的酒朝那死尸身上倒净了。
“别碰。”他把酒瓶扔给颜叔,一把抱起我。“卫生所在哪?”
“没,没有卫生所,只有个赤脚医生,姓李……”
“在哪!”
“出院向前翻过三座山,有个新建的砖房……”
没等他说完,父亲已冲进了雨里。“别碰,到厨房待着!”
山。
三座山。
冬夜冷雨中的三座荒无人烟、鸟兽绝踪的三座山。
但是,当父亲背起我,不顾一切地冲向那它们时,还有一座山,一座足以将它们碾碎的山。
父爱。如山的父爱。
父亲把警服披在我身上,又把两条长长的袖子在胸前打了结,把我固定在后背上。他甩掉警靴,扯掉袜子,手脚并用地攀登起来。
冬日硬脆的树枝戳在他身上,锋利的断面如同刀片,密密地割破了他的肌肤,渗出的血把秋衣慢慢浸透了。在最后一座山的山巅,他直起腰来,缓了口气。夜雨里,远处的山峰和广袤的大地被落雪染白,只有这一小片山坳,依旧是诡异地飘着雨丝,见不到半片雪花。父亲长吸一口气,朝山下冲去。
在两山之间干涸的河床边上,有一所不大的砖房,朝南一侧刷了白漆,巨大的红十字画在墙上,窗口里传出淡淡的火光。
“赤——脚——李!”父亲边跑边吼道。“赤脚李!”
父亲的声音如同炸雷一般。那房间里灯晃了晃,人影闪动起来。父亲窜到门正要踹门,却听见里面传出一句:
“信巫还是信医?信巫找我爹,信医找我。”
父亲抬起的腿止在了半空。门开了,一个年轻人出现在门口,手里还握着一本医学院的教材。他看着父亲的野人一般的模样,愣住了。直到他注意到父亲肩头半死不活的我,才意识到自己轻率了。他正要将父亲引进屋,父亲却打量着他,拧着眉头吼道——
“论巫论医来论人命,你不配!”
父亲暴喝惊得这年轻人浑身一震,接着,他的眼里涌出的泪花,那只白生生的、握着教科书的手抖了起来。
“你爹呢!”
“生气,走了。”
“被你气走的?”
“唔……”
“事众先要孝亲,医者要有仁心,你——”
正说着,父亲突然晃了晃,差点倒下。那年轻人正要伸手去扶,父亲却一甩手,躲开了。
“传染。”父亲嘶哑着声音说道。“找件不穿的厚衣服帮我给孩子换上。不要进屋。我去找你爹,他在哪?”
父亲解开胸前的结,把我从背上拖下来。他咳嗽着,脊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颓弯下去。没等那年轻人回话,一道闪电亮起,那年轻人骇得一把拉住了门框。在父亲身后干涸的河谷,一个身材伟岸的身影正大步走来。闪电把他照得格外清晰。那是个身披兽皮、披发赤脚的野人。
年轻人结结巴巴地指向远方,父亲一抬头,把那年轻人吓得坐倒在地上。父亲的眼神也开始涣散,眼底闪出幽幽的绿光。
父亲把我留在门口,缓缓走下河谷。踏着被流水冲刷得棱角全无的河床碎石,他迎着那身影走过去。那人跨着大步,手中擒着一根略有弯曲的长枝,树枝头上还绑着尖锐的石片。是根石矛。
“嗷呼——嗷呼——”
那人与父亲相距一米站立着,口中发出示威般的呼喊。两人个头相当。父亲衣衫褴褛,也弓着背冲他吼了起来,如同是两个相互争斗的史前人类。
父亲四下里望了望,像是要寻找什么趁手的武器。那人见状,将手中的石矛一扔,朝父亲扑了进去。低沉的冬夜滚雷动地而来,闪电不时劈开纯黑的夜幕,带来几秒的白昼。两个身影在河床上扭打翻滚,怒吼声响彻整个河谷。父亲眼底的绿光越来越盛,体力渐渐透支。终于,那人将父亲压在身下,仰天长吼起来。
一道如同鞭炮般的声音钻入夜空,打断了那人的吼声,仿佛惊得连雨都失去了声音。接着一道昏黄的光胡乱在夜幕中闪着,最终落在了那野人圆睁双眼、髯虬丛生的脸上。颜叔一手举着枪,一手拿塑料袋裹着手电筒,与挎着医药箱的赤脚李,正深一脚浅一脚地从河谷上游奔来。
“别伤他。”
赤脚李伸手拦了一下。颜叔从腰摸出警棍,递给赤脚李。颜叔端着枪,赤脚李提着警棍,两人朝那野人围了过来。颜叔正要上前,赤脚李却拉住了他。赤脚李盯着那野人,慢慢蹲下把警棍小心地放在地上,把药箱也解下放在了脚边。他高举着双手,手掌朝前,表示自己没有武器。他缓步朝前挪着,指了指被野人压在身下的父亲。此刻,父亲正挣扎着扬着头,眼中的绿光愈加鲜亮。赤脚李指了指父亲,然后又用两根手指对着自己的眼睛指了指,意思是请注意父亲的眼睛。
那野人脸色严肃地点点头,也同样用两根皮肤粗砺的手指,动作笨拙地比划着自己的眼睛。赤脚李示意颜叔把手铐拿出来,给自己戴上。颜叔不明所以瞪着他,赤脚李使了个眼色,赶紧。颜叔当着野人的面,把赤脚李的两手铐了起来。赤脚李对着野人,把手铐用力挣了挣,表示很结实。他让颜叔打开手铐,自己拿着手铐举在半空,然后指了指被野人压住的父亲。
那野人愣了愣,接着点点头。他挪了挪身子,揪起父亲的两只手。赤脚李走过去,把手铐戴在了父亲手上。颜叔正要发作,赤脚李轻声说:他病了。
三个人把父亲拖到卫生所前,赤脚李从医药箱里取出针,在父亲头上扎了几处穴位,父亲的手脚不再抽动,可眼中还是绿得吓人的光。
“嗨!”颜叔突然喊了起来。我像个木偶一般立在屋檐下,赤脚李的儿子正在给我换衣服,那野人却伸出手去,要去摸我的脸。
听到颜叔的叫声,那野人停住了,他嘴里咕哝着,缩回手来。赤脚李停下了手里的针,抬头望着那野人,问道:
“你说什么?”
那野人瞪着赤脚李,显然并不明白他说的话。
赤脚李指了指我,又指了指野人,又指着嘴,重新问道。
“Peili。”那野人说道。
赤脚脸色一变,他跳起来,抓住那野人的胳膊,大声重复道:
“Peili?”
那野人点点头。赤脚李把自己的儿子拉过来,他俩细长的脸颊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他指着自己,又指了指儿子,说:“Peili。”
那野人点点头。
他又指了指躺在地上的父亲,而后指着我,说,“Peili?”
那野人又点点头。
赤脚李指着自己,说,“Mei。”
野人点点头,说,“Mei。”
赤脚李指着野人,没有说话。等了一会儿,那野人指着赤脚李,说,“Tu.”
赤脚李又指着颜叔,那野人说,“Su.”
赤脚李两眼直直地望着野人。那野人说,“Mei Peili”,接着又做了个四下张望寻找的动作。赤脚李转头望着一头雾水的颜叔,问最近有没有见过一个走失的孩子。颜叔告诉他,今晚刚刚送来一具尸体,不是成年人。
“跟他像吗?”赤脚李指着那野人问道。
颜叔慢慢地、认真地点点头。
赤脚李叹了口气,望着那野人满怀期待的眼神,摇了摇头。
那野人抓住赤脚李的肩,大声地问了一串话。赤脚李被他摇得都要散架了,最后,他挤出一句:
“Mot.”
那野人的目光一下跌落下去,他松开手,失神地拖着两只大脚,朝河谷走去。闪电照亮了他的身影,他蹲在河滩碎石上,两只手捂着脸,痛哭起来。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颜叔问道。
“赶紧把这两个搬进屋里去。”
“老胡说是传染病,你看他这不就是被传上了?”
“屁话。不会传染咱们。赶紧。”
赤脚李的家,也是村里的卫生所。在两排阵列着药品的柜子对面,是两张用门板搭建的简易病床。我和父亲被分别放在了上面。赤脚李吩咐儿子抓了些草药,就着炉火煎了起来。颜叔蹲在炉子前,一边烤火,一边看着赤脚李的儿子用蒲扇扇火。赤脚李站在窗前,向河谷的方向望去。就着不时亮起的闪电,还能看见那野人悲痛的身影。
“老李,到底怎么回事,他俩中了哪门子邪?还有外面那个人,什么来路。你跟他嘟囔了些什么?”
赤脚李没有说话,他立在窗边有好一会儿。接着,他轻声应道:
“是拉丁语。”
“拉——拉丁语?”颜叔惊讶道。赤脚李的儿子停住了手中的蒲扇,同样惊讶地看着父亲。
“但凡学医,西医,就要学拉丁语。动乱那些年,我躲在乡下,跟着一个老道学了中医西医,甚至还有这几乎没有用过的拉丁语。”
“老——老道?”
“道人说,自己空有一身本领,天时不济,只能独善其身,传我些三流技艺。处众人之所恶,便几于道。那道人观我,说一生无福无禄又无子,原本是个修道的苗子——穷到极处,便生通达,也就是否极泰来的意思。只可惜,动乱中我虽未受苦,但也没见过这世间的繁华。有一次,我下山时遇到了个落难的姑娘。我救了她。这人凡心一起,就是神仙也不愿当了。正好赶上拨乱反正,我就想带着姑娘下山去。道人问我求什么,我说想留个后。道人说,天生天杀,你当医生,救人去吧。只可惜我福薄,大愿未行,孩子就先来了。那姑娘难产,死了,留下我们爷俩。是我对不起她。”
寂静的冬夜,雨声飘零,只有窗外男人的悲号声。赤脚李的儿子怔怔地盯着炉火,手中的蒲扇跌到了地上。
“拿伞去。给外面的爷们撑着。他也是个当爹的,刚死了儿。”
小李抹了把泪,站起身来。“爷,我这就去。”
小李从里间拿出一把精心收起的长柄雨伞,上面还盖着油纸。他推了门,撑了伞,走到那男人身后,默默地立在雨中。
“那道人……”颜叔迟疑地问道,“是不是左手——”
赤脚李一挥手,打断了他的话。“是不是他,他是不是,都不能改变什么。”
颜叔看着那炉火和壶中袅袅而起的蒸汽,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“那,那为什么,就连野人也会说拉丁语了?”
“那不是野人。”赤脚李说道,“语言与生物一样,有族谱,也会进化。跟东亚不一样,现存的西方语言,包括算上梵语,最初都是从同一门语言分化出来的,就好像今天的粤语、客家话和北方话一样。有人将那门原初的语言称为原始印欧语。在今天中国各地的方言里,最根本的词根,发音变化不至于面目全非。就比如1到10十个数,广东人说得再离谱,你也基本能听懂。印欧诸语也是。‘儿子’、‘你’、‘我’、‘他’、‘死亡’,仅凭这几个词根,跟那个男人还是可以交流的。只不过他的唇形进化得还不完全,不如我们灵活,‘腓力’的音,他只能发成‘胚力’。我猜,这并不是他的母语,而是一种入侵者的语言。”
“你为什么来这儿?”颜叔沉默了一会儿,没有接他的话,而岔开话题问道,“你不是当地人。”
“跟你一样。”
“跟我?”
“为了真相。”
“真相?”
“我当年作为文化站的工作人员,下来采风。直到误打误撞地来到这儿,我才发现这儿别有洞天。”
“别有洞天?”
“这是个神奇的地方。起初,我只是觉得他们有点怪:他们民风淳朴,但没有传说,没有神话,没有任何虚构出来的故事,也没有任何现实以外的联想。你想来这儿采风?做梦吧你。这儿什么都没有。只是呆得时间长了,才发现自己走不了了。这儿没医生,他们需要我。所以我留在这儿,用一生补一个大愿。在这儿最初的几年,我发现这儿终年无雪,地下磁场怪异。他们不与外界通婚,却始终没有近亲结婚而产生的遗传病。但是在河谷里,不时会出现陌生人。有时候是活的,有时是死的。这是老道所说的乾坤颠倒的错序之地。”
“错序之地?”
“呵,颜所啊,都到这份上了,你也别装傻了。”
“我,我哪有,哪装傻了。”
“现在大学生各单位抢都来不及,怎么会把你扔到这儿?哪个领导不爱才?可你非要花样作死,还不是为了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吗?”
颜叔沉默了半晌,终于正色答道:“老李,还是你道行深。”
赤脚李笑了起来。“你以为我去县城,除了买药,别的就什么都不干了?”
颜叔点点头,起身把陶壶从炉子上端起来,倒出一碗药,吹了吹,自己先灌了下去。
“别蹧蹋药了,传染不上你。”
颜叔鼓着嘴,含着最后一大口药,不知是该咽下去,还是该吐回碗里,再灌给谁喝。
“你跟他们不是一个人种。”
颜叔那一口药噗地喷了出来,涂了一墙。
“咳,咳。”颜叔呛得上气不接下气,他抹着嘴问道,“你说什么?”
“北京人头盖骨,见过吗?”
“嗯。”
“跟你像吗?”
“像。”
“跟他呢?”
“老胡?像啊。”
“像个屁!就你这眼神,山顶洞人没灭绝,真是奇迹。东亚人种,有这么大脑壳吗?能晚上看清东西吗?啧啧,真是奇迹。”
“他们……不是东亚人?”
“早年间,有一种说法。说现代中国人是北京猿人的后代,因为两者有很多相似的特征:平脸、高颧骨和铲形门齿。”
“这我知道啊:人类起源说的多中心假说。我跟老胡就是去生物系蹭课的时候认识的。”
“但最新的国外研究显示,从染色体来看,现代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母亲——非洲夏娃。”
“我们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。现代人类起源在非洲。”
“对。但最奇怪的是。即便是基因确凿地显示我们只有一个起源,但在中国,发现的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,只要有保存下来的门牙,全是一样的。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,7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,三万年前的山顶洞人,几万年前的河套人,都是铲形门齿。”
“趋同进化?”
“不一定。铲形门齿似乎并没有特殊的进化意义。并不是说,你没有铲形门齿,就在东亚大地上生活不下去了。”
“那是为什么?”
“我想——因为这儿。”
“这儿?”
“你不是在调查自己的身世,一路追查到这儿吗?这是就答案。这儿。”
“错序之地?”
“对。我猜,这里是个时空交集之所,那条河沟,连通着史前世界。北京人,尼安德特人,丹尼索瓦人,他们都可能出现在这儿。当然了,这里的人也可能会到史前去。这里的人,当然不是所有人,他们的虚构能力不强,不像智人那么天马行空地会想像,所以他们没有传说,没有神话,有时候看起来也更木讷。因为他们是早期智人同时代的其他人种的后代,或者说是混血后代。”
“后代?还混血?不是有生殖隔离——”
“你懂个屁!现代智人身上都还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呢。谁知道是他们哪一代混血的,还是说,是在这里混血的……”说着,赤脚李也惊讶地停住了嘴。
“但是……”颜叔沉思着说道,“他们如果真地是从那个时代而来,也会带来那时候的疾病,对不对?”
“对。老胡和小胡,他俩的病,我之前在村民身上见过。只是他们处理的方式是祝由术,也就是巫术。那个男人,他显然是知道这种病,我猜他跟老胡干那一架,是想在老胡完全发病前先制服他。过会儿,等他哭够了,我得问问他,他们是不是有治这种病的药。我早就在想,要不要想办法关掉这道错序之门——在你那张大嘴把一切都抖露出去之前。”
“然后呢?”母亲问道。
“然后,那个尼安德特人哭够了,回到屋里一顿吃了8个馒头。第二天,他带着赤脚医生到山里找草药去了。赤脚医生用那草药治好了我跟我爸。尼安德特人临走的时候,赤脚医生给了他一堆庄稼种子让他带回去。接着是他和颜叔还有我爸商量怎么才能把那道时空之门关上。”
我把经过讲给母亲听。她只是笑着望着我,最后她问道:
“你知道我去开什么会了吗?是个关于返祖现象的研讨会。其中有几个例子:有个孩子天生长着尾巴,还有个孩子浑身都是长长的毛,像小猴子一样——本该带你去听听的。会上,你王姨讲了个故事,说是开颅手术的人,有时会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,虽然被麻醉了,但却能看到整个手术的过程。有人说,那是大脑‘自己’去‘看到’的。人的大脑很神奇,会在意识停歇的间隙,为了保障自己不发疯,而去构思某种可以合理化一切经历的故事。”
母亲看着我,微微笑着。我心想,妈,你是说,这些都是我烧糊涂了,自己在脑海里编出来的?
“你最近不是在看关于尼安德特人的书吗?还有福尔摩斯什么的。”母亲补充道。
我突然感觉像是被关进了疯人院里。如果你被关进了疯人院,怎么才能证明自己没疯呢?不,你不能,你所说的、所做的一切,不论是否正常,那都是你发疯的症状而已。
“如果真相带来的只有灾难,你还非得撞得头破血流?”
我想起父亲在我“虚构的故事”里对颜叔说的话,乖乖闭上了嘴。
“多关注些现实吧。”母亲说着,揉了揉我的头发,“如果你以后当了科幻作家,给你审稿的编辑,只怕也会这么说呢!”
许多年后,我回到家乡。在某个细雨的清晨,我突然想起了多年前的梦魇。
父亲从大字版的《参考消息》后面抬起头来,略微低了低前额,从老花镜上看着我。
“那时候你多小?那些个破事儿你还记得?”
“爸,我小又不等于是傻子,怎么会不记得?”
父亲把报往桌上一拍,一把抹下眼镜,用一条磨得褪了色的眼镜腿指着我,大声说道:
“你听那小子净他娘胡扯。人家那村里当时纯粹是营养不良。后来生活条件好了,哪还有什么不正常的。人家小伙子朴实单纯,身体条件又好。现在咱县里武装部征兵,年年都瞅着他们村。”
突然,我有些怔了。我想起了那些早已灭绝的早期人类——尼安德特人、山顶洞人、北京人还有其他那些死在与智人竞逐之路上的远古人类。就像是和诡计多端的殖民者相比,印第安人显得格外单纯一样。在有些学者眼里,尼安德特人,还有其他许多灭亡的古人类,他们并不是死于身体上的弱势,也不是因为智力差距悬殊,而是亡于新兴智人的奇技淫巧和阴谋诡计。从这一点上来讲,这是似乎完全是个讽刺——
善良和单纯从进化和种族存亡的角度来讲,似乎完全不是优势。
想到这儿,我突然脱口而出:
“爸,我想再回去看看。”
“看什么看,人家好得很。那儿现在已经是影视中心了,人家开个农家乐、当个群众演员,比你工资都高。”
“所以才要去看看嘛。也看看颜叔和赤脚李。”
其实,我是在想,要怎样才能让那些早已灭绝的古人类知道,也有这样一个时代,他们完全可以与我们和平相处,和我们一起走在同一片阳光下,而不必因为自己的善良和朴实付出亡族灭种的代价。
“嗯嗯行吧。等我先问问他们所里,别赶着人家有大活动去给人添乱——你颜叔算是为那儿鞠躬尽瘁了,赤脚李么,他云游去了,现在是他儿子在那儿行医。”
说着,他挠了挠后脑勺,重新戴起眼镜、拿起报纸来,不再理我。我一低头,正巧看见几天前的一张晚报上面,是关于古桥村的报导。那上面有一张配图,是一所小学,仔细一看,那小学正是以颜叔的名字命名的。
我看着父亲那光光的大脑壳,信服地点了点头。我的舌头不由自主地舔了舔上面的门牙,笑了起来。